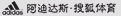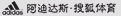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
这支“沈家军”,曾是当年唯一一支杀入世青赛十六强的亚洲队伍,曾经在和阿根廷、巴西国奥队的交手中虽败犹荣,“超白金”一代之名由此得来。可是,自卡塔尔六国赛、土伦杯、亚运会、巴林四国赛、欧洲拉练赛、卡塔尔十国赛……直到七天前,直到今天,对叙利亚国奥队这样的对手,中国国奥队竟然打得这么累、这么紧张。
光环开始退色,原先的特色打法不再,个人特点灵气也在失色,整个队伍开始趋向平庸,“超白金”一代在很多人的失望中陨落。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失望大,和期望值太高有关系。当年亚足联秘书长在阿根廷举杯向阎世铎盛赞中国队为整个亚洲足球争气的时候,沈祥福就该预见到,这以后,将一定会有“阎头”冲进休息室“狠批”整支队伍的那一天。因为一鸣惊人之后,就没有了继续低调的可能。
亚运会、中叙主场,果不其然。足协已对这支队伍期待甚殷。
不光是足协。在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已经成为一种情结、一项使命,其意义早已超出比赛和游戏本身。一代一代,为它前仆后继,屡败屡战。
当中国的一大批球迷已经习惯于“国家队不行看国奥、国奥不行看国青,大不了再看国少”时,人们忽略了一点:那时的国奥,无论是“361”的阵型战术还是临场发挥,在技术和体能上都已达到了巅峰。波峰过后必是低谷。
沈祥福难辞其咎
训练是比赛的影子。这一个多月的昆明封闭训练,几乎一成不变的训练,看得跟队的记者都恹恹生腻,也难怪队员们觉得枯燥无味,难有兴致,难出状态。热身、传接、对抗、攻防、任意球,期间,沈祥福也有讲解,不过大多局限于“以球论球”。其中,尤以无防守情况下的单刀、包抄练得最多最欢。沈祥福解释说“这是培养队员找到射门感觉”。
可即便再外行的人都想不通:有这么舒服的单刀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球应该是在跑动和穿插中接应的,而中国队的传球太过明确,接应者又总在“死”位置接球,以至于拿球队员球还没传出,对方就知道该往哪里去堵截。所以说沈祥福难辞其咎,并不为过。
都觉得国奥的训练有问题,沈祥福不会承认,外人也都不敢说,而阿里·哈恩说了。年初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看国奥打丹麦时他说:“我看过这支队伍的训练,他们训练有问题,训练方法有问题。”
都说沈祥福厚道、勤恳、固执,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好汉”。对这群自己“奶大的孩子”,哪怕再恨铁不成钢,他也会像千百万爱子心切的普通父母一样尽全力护着。但他算不上一个有水平的教练,更不是一个可以为中国足球带来奇迹的大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国奥不见了当年的灵气和胆色,沈祥福不是唯一责任人。这批球员,在他们那青涩而艰难的成长期,进入了甲A,经受了“洗礼”,他们注定无法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成长。
甲A的环境,众所周知。条件好了、收入高了、名气大了、见识广了,原先意气风发的“以梦为马”,变成了“以宝马为梦”。几次集训期间的“短路”、整风、泡吧事件的发生,暴露了这批队员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认识不足,以及“榜样力量”的匮乏。奢侈地想象一把,如果他们在联赛中,所见所闻都是如劳尔般的人品、如齐达内般的内涵,这批队员对自己的要求,一定比现在要高很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甲A的“好日子”过惯了,俱乐部和球迷“宠”惯了,球员往往容易得意忘形。既然七分力就可以了,为何要出十分?既然不用每天勤练习也可以打上主力,为什么还需苦耕不辍?国奥的不思进取毁了自己。
有句行话说,一路磕磕碰碰,反而能走得远。23年来中国足球的第七次冲击奥运就在这样的磕碰中起步,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大马士革9月18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