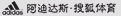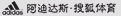本报记者黄端2002年3月15日,就在中国足球队在南斯拉夫人米卢蒂诺维奇的“快乐足球”哲学指引下,即将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圈一展身手之际,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被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以“涉嫌商业贿赂”拘留,成为中国首位被拘留审查的足球裁判。而业内的一个广泛传言是,龚建平将在本周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业内人士相信,多年以后,这一事件将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而被人们反复引用。它将成为体育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经过近10年的商业运作之后,终于纳入现代社会的象征———法治的轨道下运行的标志而被载入历史。
而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形成,显然是在媒体的一系列穷追猛打的报道,民营企业家经营的足球俱乐部无所顾忌的揭发检举,以及人大代表与专家学者的强力介入等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说,与“足球已是中国最公开最透明最民主的一个领域”(一位网友的说法)密不可分。
中国足球被称为“最公开最透明最民主的领域”,这一翻天覆地的转变,无疑是中国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投影:商业因素的主导地位、商业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权利的觉醒……而足球的一些特珠元素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如言论自由的充分展示、公众舆论与政府部门的博弈与互动等等,则更是作为社会最前沿的实践而拥有独有的价值。
正如有人所说,从中国足球身上,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发生的所有变化,还可以看到中国即将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
商业的力量
审视当下的中国足球,不能不提到十年前那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邓小平“南巡”。
1992年,在邓小平“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迈得更快一点”的指示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前身)在北京召开“红山口会议”。在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中央领导“一步到位”指示下,国家体委在会议上确定了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推出“全国足球职业联赛”。
从计划经济下的只讲投入不讲经济回报,到一步迈向市场经济,中国足球无疑迈出了“惊险的一跃”。这一跃所带来的后果,在当下的中国足球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1993年冬天,8支被称为俱乐部队的甲级队在广东集中进行了一次奇怪的比赛。然而,整个赛事仅卖出可怜的8张票。
在此之前,尽管也有联赛,但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造成的结果是,比赛“把观众给打跑了”。而职业联赛的开展,就是为了“把打跑的观众请回来”。
尽管这一努力在第一次以“8张票”的业绩惨败,但在半年以后的1994年中,中国足球拉开了它历史变革的大幕。由某跨国烟草公司赞助的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大连、沈阳等12个城市粉墨登场,并迅速成为不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大事。
转变背后的秘诀其实很简单:随着商业因素逐渐主导这项运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意识形态色彩被远远抛在了脑后,从而使其激烈程度、可看性大大增强。“世界第一运动”的真正魅力开始展现出来。
在8年职业联赛锤炼后,一家足球俱乐部商业利益的直接来源已经基本定型,它一般包括:俱乐部的冠名权、球衣胸前背后的广告、主场的场地广告收入、电视转播权以及门票收入。而中国足协也形成了自己的赢利渠道。
有了商业,才有了球星,有了球星的巨额转会费,有了球队的升降级制度,有了球迷在球场上的狂欢乃至“作秀”,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有了中国足球目前的这一切。
依然是“政治足球”?
尽管因为商业因素的介入和主导,才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巨大变化,然而,政治因素显然并没有彻底淡出中国足球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足球至今依然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政治足球”。
支持这一判断的最明显的个案,是1999年甲A联赛中大连市政府的现。1998年,大连万达将著名后卫孙继海以50万英镑的价格转会到英格兰的水晶宫队。次年,大连万达实德队在甲A联赛进入中盘时已陷入降级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大连市政府拨出了1000万元人民币,替万达赎回了孙继海。理由是,“万达实德是大连市的名片”。
某某球队是某某城市的“名片”,是商业化时代足球再次泛政治化的一个标志。“政治足球”的另一个证据,是各足球俱乐部的赢利状况。
按照业界公认的说法,迄今为止,保持赢利状态的足球俱乐部屈指可数。以2001年为例,有媒体在当年的甲A联赛开打之前为各俱乐部的财政状况算了一笔账:比如,算上转会费、主场广告费、球员胸前背后广告以及球票收入,云南红塔队的总收入预计为1500万元;而赢球奖金、球员工资以及其他开支加起来,红塔集团对该队的计划投入将达4000万元;沈阳海狮队当年的收入预计达3500万元左右,总投入则在4000万元左右;重庆力帆队的总收入为2200万元,总投入则在3500万元左右……
显然,从经济层面推算,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都呈现亏损状态。那么,企业为什么还愿意在连年巨额亏损的状态下进行足球经营?
尽管也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扩大企业知名度、看好将来的足球产业等,但是,看到某些地方政府将足球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从而寄希望于以投资足球的方式获得当地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支持,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真正的原因,早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商业资本必须与权力资本相结合,才能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社会转型期的经济规则,早已成为不少涉足足球产业的商人的信条。
红哨、黑哨及假球
在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进程中,“商业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力量始终处于不断搏斗与消长状态中。而如果法制匮乏、制度缺失、监督乏力等转型期普遍存在的诸多社会缺陷共同作用,则极容易导致同一个结果,那便是:腐败,以及使腐败成为圈子内的基本运作规则。
对此,足球圈内分别用“红哨”与“黑哨”来形容。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曾在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呆过6年、当了4年总经理的戴大洪对此知根知底。
做裁判工作,“开始时只是请吃饭,送运动服,后来送烟送酒,再后来就变成送钱,10块、100块,再到成千上万。”戴大洪说。
1996年河南建业在同深圳的比赛中,因为有争议的判罚落败,董事长在比赛结束后只说了一句话:“以其人之道。”
“起初只做个别场次个别裁判的工作,到了1998年,这已经成了一个例规。”戴大洪说。后来就演变成送钱只是为了裁判能公正地执吹,因为无法确定什么情况下裁判才会对自己做出有利的判罚。
以至于有一个荒诞的说法是:“俱乐部对裁判也实行年薪制,一般会在年初或者年底给裁判送钱。”
据知情人士透露,每个俱乐部都有专人做裁判工作,一般来说由俱乐部副总与竞训部负责。1999年初,就有媒体披露,上海某甲级俱乐部的账目上有100万元的“裁判接待费”预算。
除了金钱之外,执哨出问题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原深圳金鹏俱乐部老总利焕南曾说过,“中国没有黑哨,只有官哨。”而有过多年教练生涯的陈亦明也曾经说过,“中国足球没有黑哨,只有红哨。”
戴大洪举了一个例子,1996年,某有背景的球队一年冲A成功,其中不到一个赛季就获得了14个点球。
黑哨和官哨、红哨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驱动前者的是钱,是经济利益;而驱动后者的则是人情和权力,是足协的“大局观”、“内部意向”。
反过来,“在足球圈里混,裁判不收钱是不可能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总会收的,要不就不可能在圈内混下去”。
和黑哨相伴相生的,往往是假球,它的危害甚至比黑哨更甚,因为制造假球的本身,是足球比赛最直接的参与者:教练以及球员。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98年的“隋波事件”。
1998年8月22日,甲B联赛第16轮,云南红塔对陕西国力。当前者以3比2获胜以后,当时陕西国力队的主教练贾秀全在比赛结束后称这高原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场外的干扰太大了,并且场上有球员发挥失常。面对“哪一位”的追问,贾脱口而出“3号隋波”。
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很快,足协就组成了调查组,并牵扯出一盘由国力俱乐部掌握的录有巴西华人王素徽企图收买国力三名巴西球员的电话记录的录音带。但是,经过131天的调查后,足协称证据不足,“隋波事件”不了了之。而手握“电话录音”证据的陕西国力队则在当年顺利保级成功。
不堪重负的“3号隋波”后来退出了中国足坛。
据说那年冬天,有人看到大雪纷飞中隋波一个人站在足协大楼外边,等待足协官员的召见。而《足球》报的一位资深编辑当时在上海也见到了贾秀全,向他表明《足球》在打假上会全力支持,希望他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贾说:“不能再往下谈了。”
同在1998年,还有一个外国人惊世骇俗的声音被电视镜头留在了中国足球史上。河南建业队的罗马尼亚外援尤里安在球队降级后面对镜头说:“中国足球toomoney,河南建业nomoney(中国足球太多的钱,河南建业没有钱)!”
“用脚投票”权的胜利
虽然依然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商业元素的深度介入,毕竟还是给足球领域带来深刻变化。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商业契约关系的确立所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同样是在那家媒体给去年甲A各俱乐部的财政状况计算中,可以看出作为足球产业至关重要的组成群体——球迷的贡献率。
以球迷最直接的贡献———球票为例,上海申花的门票收入预计在1000万元以上,沈阳海狮的门票收入预计为400万元,重庆力帆的门票收入预计也为1000万元左右。显然,门票收入是俱乐部收入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有的俱乐部来说,更是占到了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如果算上广告等以球迷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支出,则俱乐部的绝大部分收入均来自球迷。这种商业关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千百万球迷开始感觉到,自己是那数十家俱乐部、数百名球员、乃至于中国足球的管理和联赛的经营机构———中国足协的“衣食父母”。他们觉得,如果自己对俱乐部的表现、对中国足协的表现感到不满的话,完全有将这种不满表达出来的权利。因为,他们拥有最基本的制约手段———“用脚投票”。
而与此同时,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进程也诞生出越来越多以球迷为主要读者的足球和体育媒体。据说在1992年前,哪怕是开全国会议,专门的体育记者要凑一桌都难。而现在,据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专业足球记者就有6000多名,加上没有注册的,共有8000多名“足记”。加上今年是首次有中国队参赛的世界杯年,足球传媒的膨胀是必然的。
毫无疑问,千百万球迷也是这些8000多名“足记”、近百家体育媒体的“衣食父母”,他们同样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当球迷对球队表现感到不满的时候,他们发出了其他领域并不常见的呐喊———球场上此起彼伏的“下课”声。而众多体育传媒和足球记者,为了争夺球迷的“眼球”和“投票”,则必须充分反映球迷的诉求,千方百计挖掘独家新闻,揭露“足坛黑幕”。
就这样,这种纯粹的商业关系,实际上反而带来了球迷与俱乐部、足协以及足球媒体等多方的权力制衡和互动关系,从而为形成“最透明最大胆”的舆论氛围奠定了基础。
这种关系的确立也并非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1996年,供职于中国足球报社的马德兴痛感国奥的失利,在上海的《新民体育》上发表了质问中国足协的《中国足球十问》这样一篇战斗檄文。这篇文章直接导致了马德兴的离开,而《新民体育》的主编徐世平也因此“下课”。
同年,原来在四川体育报当记者的李承鹏因为发表了一篇名为《斩断黑手》的批评黑哨的评论,也被迫离开了报社。
1997年11月,在中国队十强赛失败的第二天,国家体育总局的新闻司负责人提出了“二流论”,即《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
“‘二流论’的实质就是认为中国队冲出去是不正常的,不出去才是正常,并不是工作没有做好。”当时的《足球》报负责人严俊君在报上特地组织了反击“二流论”的专版。最后还对读者来稿进行了评奖,获得头奖的是南京市委党校的哲学教授陆剑杰,除了稿酬之外,他还获得了额外的5万元奖金。
《足球》报对“二流论”进行批评的“负面影响”很快就显露出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中国足协就没有给《足球》报去法国世界杯的采访名额。“这个时代,还有谁能阻挡我们出去呢?当我们5名记者自己去到法国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到艾菲尔铁塔下面照一张相,然后发回国内,登在了报纸的头版上。”
在1998年“隋波事件”发生后,《足球之夜》曾经在节目里搞了一个计时,每次节目一开始,主持人都会提醒球迷,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多少天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足球之夜》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计时停止了。
“我们当时是挺勇敢无畏的。”刘建宏说,“但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说社会进步是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发展的。”
然而,在不屈不挠的多回合的博弈过程中,新的均衡关系毕竟开始逐渐确立。
龚建平事件:从舆论监督到司法介入的一个标本
在多方的权力制衡与互动下,龚建平事件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前一天,为了争夺仅存的一个升A名额,甲B联赛爆发了大规模的假球风波,并且也间接引发了绵延至今的黑哨事件。很快,中国足协就对涉案的“甲B五鼠”作出了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罚。
正当大家以为“假球风波”可以划上句号的时候,两个介入足球经营、但显然不愿忍受“黑幕”的民营企业家的“放言无忌”,加上众多媒体的强力介入,使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2001年12月11日,冲A未遂、进入足坛才8个多月的吉利在广州宣布退出足坛,在给媒体的公开信中,吉利自称是“无助的风中之烛”,注定要熄灭在这黑暗之中。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声说:“中国足球有很多内幕别人都不知道的,你们媒体应该有责任做到让司法机关都知道,这样才能把中国足球引入光明。”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吉利退出进行了报道,但很快,李书福身上的斗士色彩就被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所遮盖。
2001年12月14日,众多媒体共同见证了李书福、原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和宋卫平在杭州联合召开的“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上,三人自曝“污点”的同时,批评矛头更是直指中国足坛的管理者中国足协。
2002年1月5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足协对一些涉嫌“黑哨”裁判的调查取得突破,已有裁判承认“自己过去做错了事”。
“做错了事”?对中国足球有着深切理解的媒体开始担心这次扫黑仍将以拒绝司法介入、关上门私了完结。大家都意识到,必须有更强有力的部门介入,比如司法为“黑哨”定性。
1月7日,宋卫平把在去年甲B联赛执法中涉嫌收受该俱乐部“黑钱”的裁判名单交给了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马上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内参,并在次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体育活动不允许有腐败行为》。
这份“新华社内参”,一下子成了坊间争议的焦点,内参给足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相信阎世铎但不相信足协”的绿城也试图通过非官方以及非专业的权威的第三方媒体“说话”。1月10日,本报在头版刊发了记者杨海鹏的文章《中国足球有多黑》。
传媒的报道终于带动了专业人士的关注。1月11日,北京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十余名教授、律师、检察院和法院人士召开研讨会,着重讨论黑哨裁判场外收钱构成何罪、司法能否介入和司法解释能否尽快出台等问题。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认定裁判收钱构成受贿罪。
1月23日,阎世铎在北京召开的通气会上说,中国足协打击“黑哨”从不手软,并称黑哨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在通气会上说:“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他们。”
一直寄希望于中国足协能够“杀无赦,斩立决”的公众和传媒大失所望。
而后在各地召开的“两会”上,黑哨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徐美琴、陈培德等29位代表向浙江省人大递交了《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扫黑打假斗争》的议案。北京市有代表提出只有从体制改革着手,“黑哨”才可能消除,体育才会健康发展。率先“发难”的广东人大代表也提出,如果司法机关在今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之前仍未有实质行动介入调查黑哨问题,他们将提出询问或质询。
终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专程赶到杭州,参加了人大代表讨论。2月25日,最高检就黑哨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
“专门为几百个人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在历史上这可是第一次。”新华社记者杨明说。
呼唤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在媒体和公众的合力下实现了。“龚建平并不是最坏的,司法介入选择他作为突破口,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上线索多,好突破。”一位知情人士称。
“如果没有传媒持续监督的积累,并引起了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公众强烈关注的话,那么黑哨事件真的有可能会不了了之。”杨明说。
广东足球:中国足球的真正未来?
毫无疑问,龚建平事件应该成为中国足球和传媒监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很难说,在龚建平事件之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就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评论家赵牧把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分成了四种类型:“第一种,官办足球,比如山东鲁能,就是山东电力系统的国有企业。第二种,亦官亦商型,比如上海申花,它在经营上自主色彩浓,但是在招商引资上却有优势。第三是交易型的,如原来的沈阳海狮,原来的大连万达、今天的大连实德,都是企业出钱经营,政府给行业优惠政策。第四种是民办足球,比如原来的广东宏远,领导只是口头关心,而要条件却不给。”
很多人都对广东足球的衰落表示不解。广东足球最鼎盛的时候是1996年,当时曾拥有6支甲级球队,分别是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广州松日、深圳飞亚达4支甲A球队,以及深圳金鹏和佛山佛斯弟两支甲B球队。
而目前,则仅存深圳平安和广州香雪两支甲级球队了。原因很简单:无利可图。
仅以俱乐部的灰色成本为例,如1999年的“渝沈之战”,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场涉及到升降级的比赛,买家至少要花费300多万。而青岛颐中海牛队的总经理秦宁说的一段话曾经在央视被反复播放,他说:“1998赛季靠什么保的级?还不是靠颐中的钱吗?”他自己也承认颐中论实力该掉级,所以,今年目标是保级,成功了,明年还是保级。
所以,有人说,在中国玩足球,你不具备背景,根本就玩不起。
而在广东,政府根本就不给俱乐部提供这种背景的机会。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在吉利升A的关键时刻,有人问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政府支不支持。林树森说,现在足球职业化、市场化了,这个事就交由市场去解决吧,我们政府不出面。
这时许多人才想起,这么多年,从来只听说别的省市有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而在广东却是闻所未闻。
据说去年吉利退出足坛的原因除了冲A未果之外,更深一层原因是因为吉利原来生产的轿车排气量都在1.0以下,而这些车无法在广州上牌!于是,作为精明商人的李书福,自然不会做这种光掏不赚的事情。
北京青年报的王俊认为,“中国足球的明天,正是踩在广东足球的衰落的身躯上前进的。”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