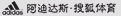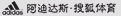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 中国体育报:追求--珠峰登山健儿的故事 |
 |
 |
|
2003年6月4日08:13
中体在线
|
 |
珠峰又开始渐渐地显露出了她清晰的模样,当初升的太阳把第一缕阳光洒向珠峰的时候,云雾正在缓缓地散去———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我们将在这一刻离开珠峰大本营。
5月26日,整个营地里的人都早早地起了床,匆匆整理着各自的行装。可就在把背包放进车里的时候,每个人都不由地要再望一眼这座相处了近两个月的山峰。
49天———从4月7日开始进驻大本营,队员们沿着这座山峰的东北山脊上上下下地踩下的一连串的脚印,记录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望着那触目可及的顶峰,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内心感受。
顶峰的诱惑
遥望上去,珠峰之巅似乎永远都让人感到变幻莫测,时而云遮雾罩、时而旗云飞扬,能够靠近她、并且最终“山登绝顶我为峰”,自然是每一个登山者的最大愿望。
为了成功完成这个目标,这个国内首支由业余队员组成的登山队,从3月29日进入拉萨开始,随着海拔高度的逐级升高,就一直在适应着高原反应,用了一周时间才来到大本营。随后经过一号营地(海拔5500米)、二号营地(海拔6000米),缓缓地上到了前进营地。
可在尚未开始正式攀登之前,进行了第二次高山适应性行军之后,陈骏池就说,真正地接近了珠峰之后,登顶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可要是说一个登山者对登顶的心情很平淡,会有人相信吗?”
在成功登顶后,陈骏池说,在向顶峰进发的过程中,也的确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尽管在向上行进的队列里,他始终走在队伍的第一个,可一路上想的最多的就是抓好路绳,稳步走好脚下的路。直到接近顶峰时,看见了上面有人,感觉顶峰马上就要到了的时候,才有了短暂的兴奋的感觉。然而实际上,还要再上上下下地翻过两三个雪坡之后,才是真正地接近了顶峰。“登山,就是件磨人性子的事,”他说,“在峰顶上做完了我预先准备好的几件事之后,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安全下撤。”
对此,中国登协常务副主席李致新说,每一个登山者的目标都是要登顶的,然而每一个成熟的登山者都绝不会把登顶作为惟一的目标。
风中的考验
“也就怪了,按照以往珠峰地区的天气规律,5月份肯定是天气最好的季节,”罗申说,“可今年4月的天气却出奇的好,风也小、天气也比较晴朗。”
罗申,中国登山队副队长,也是这次登山活动的先行官。自3月12日中国搜狐登山队正式宣布成立之后,罗申就带着18名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来到了珠峰脚下;展开了选址建营的工作。在建大本营的时候,除了为平地面、来来回回地搬石头比较累一些以外,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在这种好天气下,罗申还指挥着夏尔巴协作人员完成了一项“艰巨工程”:在紧挨山坡下的乱石堆里挖坑围栏,建起了一个应急公厕,特别在其中挖出的一个直上直下、深达1米多的粪坑,尤显难度之大。
可过了4月26日,在队员们完成了往返北坳营地的适应性行军之后,天气就开始逐渐转坏。在完成了一次在北坳的高山适应性行军之后,4月30日,当第一组队员刘福勇、陈骏池和李伟文/梁群夫妇在队长尼玛次仁的带领下向海拔7790米挺进的时候,当晚就遭到了暴风袭击。
从第二天开始,高海拔上的大风逐步也席卷了下面的营地,第二组队员由北坳营地向上跟进时被大风击退。全体回到前进营地后,攀登前方总指挥王勇峰考虑到前进营地大风不利于队员休息,决定继续回撤大本营。谁知,大风已赶在他们之前扫荡了山下的营地,一号营地和二号营的帐篷都被吹得没了影,大本营也被狂风摆平了近二十顶军用大帐。
从5月2日到9日,无论是大本营还是6500米的前进营地,皆连续出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风。刘福勇和陈骏池在回到大本营的当晚再遭风袭,三更时分拎着睡袋四处投宿。
大风打乱了登山队预先为队员们准备的多套高山适应计划。由于没有一名队员得到8000米以上的行军经验,更多的行军艰险和心理考验都被集中到了后来的正式攻顶期间。
攻顶的艰险
连续不断的大风在5月9日间歇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停,时强时弱地变得更难把握。在珠峰地区,没有哪一个气象机构敢自诩准确预测出这里的天气变化,但任何一家的预测都足以影响前线指挥部的决策。
5月11日,登山队从大本营重新出发,正式向顶峰进发。从这一天起,狂风聚起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而且其规律也越来越无章可循。
5月14日,第一攻顶突击队队长尼玛次仁带队来到北坳营地后,依据瑞士队的天气预报,请求把原定在5月17日和18日两天内的攻顶日提前,因为据称这两天会起大风,而中间的5月16日很可能是一个大风间歇的好日子,为此,尼玛提出了带队直跨8300米突击营地,然后抓住时机直接冲顶的大胆想法,经过近三个小时激烈争论,尼玛的提议最终被王勇峰力谏劝止。
尼玛之后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第二天北坳起的风就在九级以上,根本无法继续向上行军,而且后来真正冲顶时,在8300米以上路线的艰险程度也“超出了我想象中的十倍”。
其中有两处路段,尼玛认为对所有的登山者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一是“第二台阶”处的那个“中国梯子”,由于梯子上方还有两块相互挤对着的巨石,难以接近“台阶”的上沿,因此在上到梯子顶时必须抓住侧上方的一根保护绳,蹬住侧后方岩石的一壁,再跨上对面的这块巨石,难度很大;其次,就是在接近登顶时“第三台阶”的侧下方,有一段近30米长、在峭壁上横切的路段,这时一段借着层状岩伸出来的岩缝、在崖壁上打出保护绳索做出来的一条路,实际的路宽只能仅仅放下一只脚,一侧是贴着崖壁用岩锥固定的绳索,一侧则是垂直落差深达2000多米的悬崖。
尼玛说,在上了“第三台阶”以后,比大拇指还要粗的路绳,很多由于风化只剩下了细细的绳芯,很多队员都要用“快挂”把一堆绳芯扣在一起才会有些安全感。
顶峰下的抉择
登山队第一冲顶突击队5月15日回撤到前进营地后,进行了最后的休整。指挥部综合各个方面的气象资料,最终将冲顶日确定到了5月21日和22日两天。
与此同时,指挥部还多次强调了冲顶的“关门时间”问题。因为在珠峰发生的多次山难都是在下撤的途中,而这又大多是由于登顶时间太晚而造成的。在珠峰,一个最基本的天气规律就是,一过中午就肯定要起风。据说,这次在中国队里给王石担任高山协作的夏尔巴扎西次仁就是1996年珠峰山难时的参与者。当时霍尔等几位著名登山家带领的队伍在接近顶峰时就陷入了失控状态,人们忘记了时间,都要冲顶,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才陆续登顶,结果天气大变。作为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扎西次仁有幸提前一步从南坡下了山,但由于在暴风雪中能见度极差,他也是一直走到半夜云开月现的时候,才找到了营地。
这一次,冲顶队员中第一个遭遇关门时间的是李伟文。由于是最后一个钻出帐篷来套冰爪,本来就出发晚了些,再加上对走夜路的不适应,李伟文与大队落出较长的一段距离,并且中间隔着中韩联合登山队的6名队员,在过了“中国梯子”后,他就已经与前队相差了1个小时,因此他尽管有些心存不甘,但还是顺从地接受了王勇峰要求返回的命令。他说:“我当时体力很好,也有能力登顶,但登山应该服从指挥,登顶不是惟一目的。”
而当被称为“老年组”的第二突击队准备实施冲顶的时候,几乎是集体面临着对于顶峰的抉择。当时第二组从7790米营地来到突击营地时,行军用了近十个小时,比第一组同样的行军慢了近三个小时,所有人都为他们第二天的冲顶感到担心。此外,一名英国队员小腿骨折,需要救援,第一组成功登顶的陈骏池下撤路上由于胃疼病发,需要接应。这些事情都需要第二组分派出高山协作力量,第二组冲顶队伍必须主动减员。
所有第二组的队员都在帐篷里默默地掉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身体状况被认为一直很好的刘福勇主动表示,放弃登顶,随后就对着大哥王石放声痛哭。一向不善言语的张梁也在一直默然饮泣,到冲顶队员们开始准备行装时,他也做出了参与高山救人的表示。
下撤中的经历
作为第二组的队长,在冲顶过程中罗申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他比刘建、王石晚了近40分钟登上顶峰,而且在下撤的途中他把所有的高山协作人员都派给了身体虚弱的刘建和王石,因为三个人冲顶前的这一晚都没有休息。
就这样,罗申独自走在下撤队伍的最后面,在到达8400米左右时他的氧气瓶里没有气了,昏昏沉沉地,罗申说:“当时听到对讲机里说,有三个夏尔巴越过突击营地上来接应了,再加上也能看见突击营地,就找了个地方歇了下来。”
罗申并不知道,他就在这背风的地方昏睡了过去,他的身旁就是一个早前外国山难者的尸体,直到前来接应的夏尔巴发现他、给他换上氧气并唤醒他。他事后分析说,有可能身旁那位遇难者死前的情形跟他差不多,要不,不会坐在离营地那么近的地方死去。
而这天的一早,张梁就随着尼玛护送英国伤员下山了。路上,身体虚弱的尼玛在8000米左右倒下时,张梁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尼玛。张梁回到大本营后说,高山救人同样是件挺有意义的事,虽然无法与登顶去进行对比,但还是觉得非常值得。
刘福勇因为自己的高山靴被登校的小阿旺穿错了,只剩了一只自己的鞋和一只小鞋。只好这一天都在帐篷里陪着登顶下来的陈骏池。他说:“没登顶是很遗憾,但是山还在那儿,我大刘也还在,以后我还会再来登”。
李致新说,随着登山运动近几年在国内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登山者的层次也提高得很快,登山的境界追求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他说,“我们当初就没想过这么多,当年让我放弃登顶去营救一个日本人时,我差点恨得都想打那家伙,怎么偏偏这时候受伤,误我大事。后来回过头看,就发现那会儿头脑太简单了,一心光想着登顶,别的什么都没有。其实,登山本质就是一种精神,最终就是一个对高尚精神追求的体验”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