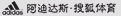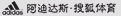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世界死于游泳的人数约为30万,而死于登山的人不超过300人。当然,这并不说明登山不如游泳危险,只是因为参与这两项运动的人群基数不一样。
登山是一项探险活动,它存在受伤和死亡的可能。所以它比别的“游戏”规则更多更细致。坚守这些规则的人,到达山巅,告诉人们那难以到达的地方有怎样的风景;但也有人,把高山的秘密永远埋藏心底,不能踏上回家的道路。他们或者因为大自然无法抗拒的力量,或者因为攀登中的意外,或者因为团队发生了问题。
这就是登山中最无情的两个字:山难。仅仅在珠穆朗玛峰上,就已有近200具登山者的遗体常年陪伴着无言的冰雪……
真正地认识登山或许应该从山难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1996年,我开始采访中国登山队,1997年底跟着李致新、王勇峰去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那一次严重的高山反应让我对自己彻底失望,但也让我再也没有离开山一步。
1998年7月18日,梅里雪山。明永村一村民在上山喂牛回家的路上,发现海拔3800米左右的明永冰川上散落着大片五颜六色的东西。他怀疑那是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部分遇难队员的遗物、遗骸。于是8月3日,中日联合调查小组到达该处,开始了清理和搜索。作为调查小组的一员,从此,我脑子里关于登山的种种美好而且浪漫的想象,统统开始改变了。
这一段冰川宽100米,长500米左右,坡度不大,较为平缓。当年的遗物、遗骸,随着冰川运动经过7年半的时间由5100米的3号营地几乎整体地移动到了3800米左右,崩落到这个“平台”上,散落面约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
搜索队队员袁红波说他第一眼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碎片时,心里一阵发麻。他捡起的第一件遗物是日方队员工藤俊二的日记本,里面写得密密麻麻的,有玩扑克牌的成绩、有喜欢的歌词,记录了一个20岁大学生在雪山上曾经的快乐时光。在4天后的遗物交接仪式上,工藤的姐姐捧着这个日记本含着泪笑了。
而李致新、于良璞和罗申一眼望见了两条蓝色睡袋。
对于李致新来讲,那蓝色太刺眼了。1988年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峰时,他们队每人发了一条这样的睡袋。那么这肯定是宋志义、孙维琦两位老登山。两具遗骸相距30米,由于冰块的挤压,早已面目全非。但于良璞肯定地指着身材稍长一些的说:“这是孙维琦。维琦1米83,宋志义1米74。这件灰白格衬衣,是维琦最爱穿的。” 他们太熟悉自己的战友了,判断结果和3天后大理市公安局法医的鉴定完全吻合。
?我没有得到许可,不能站到冰川上,只能在破碎的冰川边缘上遥望那些碎片。和我在一起的是小向导尼玛登珠。这个17岁的男孩是冰川脚下明永村的老乡。他说:“那些人心里很难受。”
“他们哭了吗?”我问他。
“没有,脸色不好看,那些人都是他们的朋友嘛。”
“雪山会爱他们的。”尼玛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并不愿意有人登他们的神山,而这一天,他开始向雪山祈祷:“别下雨了,爱他们吧。”
第二天下午15∶55,当木世俊把找到的最后一具遗骸背出冰川放在安全地带的时候,明永村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晚上6点,中日调查小组结束了整个搜索工作,从山上背下来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21份骨骼标本,日方准备带回去作DNA检验。
李致新说,给17个兄弟也准备些吃的吧。于是小背包前堆满了饼干、小食品,还有17支香烟,其中一支是国产烟,因为孙维琦就喜欢国产烟。17支蜡烛,17支香,17朵鲜花,在梅里脚下静静缅怀。不远处,篝火点燃了,饭菜的香气也传播开来,生死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其实谁也无法确切地描述,1991年时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梅里变幻莫测的气候和独特的地形使它迄今依然保持着“处女峰”的神秘。这个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与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性、海洋性现代冰川。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梅里的冰川运动非常剧烈,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从1987年首次攀登以来,每次登山者都是挥泪而别。
1991年 的1月5日下午,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报告,“在梅里雪山3号营地的17名中日队员与大本营失去联络”。 17名队员人手一台报话机,不可能全坏,他们认为3号营地发生了意外情况,最大可能是突发冰雪崩,请求北京给予支援。
当时登协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但是,梅里没有地面导航和补给,直升机不能用,救援队只能从地面进入山区。偏偏那几天大雪纷飞,救援队在深达一两米的积雪中艰难地前进,却只能登达2号营地。
军派出的高空侦察机几次飞临梅里雪山,拍摄了3号营地位置的照片。从照片上显示的一片新雪堆积的痕迹、冰层的面积来计算分析,有近30万吨的冰雪从山体上崩落完全覆盖了3号营地。
1月23日,距大本营与3号营地中断联络已经整整20天,中日双方只好沉痛地向新闻界宣布终止救援和取证工作,并对17名中日队员失踪的事故做了初步判断:“l月3日和1月4日间,3号营地上方发生特大规模的冰雪崩,将3号营地掩埋,17名中日队员(日方11名队员全部,中方宋志义、孙维琦、王建华、李之云、林文生、斯那次里)全部遇难。”
?我手边有这样一份记录:1991年5月,中日搜索队统计,梅里一天内发生大小冰雪崩达80余次。而据我观察,1998年8月4日,调查小组在冰川上工作的近7个小时里,就发生了大小冰崩十余次,其中,最大一次延续时间30秒,有的冰块甚至直接落到我的脚跟前。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所选择的3号营地正好处在受到雪崩威胁的地带。“他们明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将营地选在这里?”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披露了当时的一段隐情。中日双方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日方为了向上攀登时节省体力,极力主张营地靠近山脊,而中方则认为越靠近山脊危险性越大,主张营地远离山脊。后来双方各让了一步,中方把理想营地向上推进了几百米,而日方则下移了几百米。
其实对3号营地存在的潜在危险中日双方是有共识的。在1990年2月,中日联合侦察选定这条攀登路线时,曾在报告中指出“设3号营地时要注意上方危险。” 而且12月20日,3号营地刚建不久,一场雪流几乎波及此地。在登山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12月20日,梅里雪山第2第3支脊发生了雪崩,雪崩的尘雾覆盖了3号营地。雪崩的堆积物距3号营地约有200米。其间有一道大冰裂缝相隔,估计再大一点规模的雪崩也不会影响到3号营地的安全。”看来,争论后的中日双方都没有把这次雪崩作为一种预警。悲剧就这样“偶然”地发生了。
8月10日,搜索队把找到的10具遗骸带回大理,这些遗体在大理火化,等待他们的是已苦等了7年的亲人。
林文生的爱人和永梅家就在梅里脚下。林文生走得匆匆,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孩子——一个3岁就会认字、现在已经上学的女儿。和永梅常常抱着女儿望着山,她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登一次山,不管是梅里还是别的。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大山,不回头。她说:“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真正失去了他,以前总感觉他是出远门了。”
斯那次里的3个孩子都长大了,大儿子16岁,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能带弟妹、干零活了。可是,如果让他母亲阿玛追说说梅里,阿玛追的脑袋立刻摇得像拨浪鼓。斯那次里是个电影放映员,阿玛追看的电影都是丈夫放的。而今7年过去了,她再没看过一场电影。她说雪山太可怕,儿子不能去。
说雪山不可怕的是孙维琦的妻子赵小欣。她说那山看着很亲切,毕竟是留过亲人的地方。因为梅里,每一个登山的人、每一次登山她都会关注。因为丈夫爱山,他们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孙岩,一个叫赵岩。
7年,于人的一生是转瞬即逝的,但对于17勇士的亲人却仿佛重活一次。7年,他们的亲人华发丛生,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
从梅里回到北京以后,跟赵小欣一样,山成了我最牵挂的一个字眼。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喜欢往登山协会跑,听那帮老登山讲雪山的故事。2000年5月12日,和往常一样,我抽空溜到了登协,恰巧坐在传真机旁。突然,和以往一样的嗒嗒声传送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北京、广东两个商业登山队的5名队员在玉珠峰南坡失踪了。
登协秘书长于良璞是个活动档案馆,几乎所有的山峰资料都装在他脑子里。“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玉珠海拔仅6178米,其南坡路线清楚明了,几乎没有技术要求,是国内公认的初学者最佳启蒙路线。这条路线怎么会出事?”在他找玉珠照片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地这样自问。
这次山难恐怕是我采访登山活动以来写作最痛苦的一篇稿件。我老是在想,让遇难者的家属在媒体上得到失去亲人的消息是不是很不人道?而且我的脑海里开始无法遏制地循环演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1996年5月11日,是珠峰攀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11个人永远安息在珠穆朗玛峰的风雪之中,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向导罗勃·霍尔也是其中的一位。
下午6点20分,珠穆朗玛峰南侧海拔8600多米的雪坡上,高山向导罗勃·霍尔接到他的朋友柯特的呼叫,柯特告诉他,他的妻子打来卫星电话,等着他接。霍尔说:“等我一分钟,我嘴巴干干的,我想吃点雪再跟她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重新传了出来:“嗨,甜心,但愿你躺在床上盖得暖暖的。你好吗?”
他的妻子阿诺德说:“我说不出有多么想你!听起来你比我预料的好多了……你冷不冷?亲爱的。”再有两个月,他们的孩子就要出世了。
“就眼前的环境和高度来说,我算是舒服的。”霍尔尽量不吓着她。
“你的脚怎么样了?”
“我没脱下鞋子检查,但我想我有点冻伤……”
转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