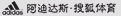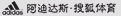以奥林匹克的名义贩卖文明
如果有机会去粉饰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很少有人会不乐意;如果有机会去装饰奖牌的背面,很少有国家会放弃 ,他们一股脑地把文化、历史、民族性都搬了上去,迫切而激动地讲述着一段段故事,努力推销着自己……
■记者张晶 赵可 任宏超
如果正面过于直白和单一,宁愿选择背面,那儿总藏着一份神秘的向往,好似有故事的人,背影足以告诉大家一切,或沧桑、或得意,或者娇羞。
奥运会奖牌也是一样。不谈1896-1924年那7届奥运会奖牌图案的原始和不确定性,自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以来,奖牌的正面图案就没有变过,意大利设计师朱塞佩·卡西奥利的杰作,左手握着棕榈叶,右手高举桂冠,端坐战车凯旋而归的自由女神和作为背景的古罗马大竞技场像标签一样深刻在往后的76年里,直到2004年的雅典。至于背面,则必须感谢德国现代主义建筑派别“Bauhaus”的代表人物格哈德·马尔克思,在他1972年为慕尼黑奥运会设计双胞胎图案以前,奖牌的背面一直都是卡西奥利设计的,被群众高高举起的冠军图案。1972年绝对是一个想象力的分水岭,在它以后,各主办国都按照需要在奖牌背面绘制不同图案,比拼着各自的创造性和历史文明。
我们这个时代离那种诗化的唯美情节已经越来越远了,因此,单纯从美学角度去看奖牌背面图案的美丑总会显得那么幼稚,事实上,它们背后的意义和故事有意思许多。
雅典,悠远而正统的自豪感
7月2日,雅典奥委会主席扎斯卡拉基展示了2004年雅典奥运奖牌设计图,那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正面坐立的胜利女神站了起来,还插上了一对翅膀,而背景的古罗马大竞技场局改为了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内部全景和雅典卫城远景;至于背面,希腊人选择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会标、五环标志、奥运火炬以及古希腊谚语。尽管,活到今天应该有140岁的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老先生创办了现代奥运会,但如果再往前挖个2780来年,奥运会归根到底是还是希腊人的东西,那一连串谚语蕴涵的或许就是一个悠远的传说。
尽管我们得说追求大一统的古罗马文明比崇尚城邦自治和商业自由的古希腊文明多了几分泥土气而少了些许海洋味儿,但别说是奥运会,其实,就是后来成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罗马文明这个巨人也至少有一条腿是站在古希腊人肩膀上的,就好象古罗马建筑的5种柱式(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塔司干和组合)就有3种(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来自古希腊。因此,对于希腊人来说,用雅典卫城和帕纳迪奈科斯竞技场来代替大斗兽场,用希腊谚语来表达观点和特色,完全不需要不好意思,他们只不过在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显然,对于古罗马人,希腊人会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抛开被征服的历史不提,单单是古奥运会的消亡,古罗马人就得负相当大的责任。尽管自从波罗奔尼撒战争后,这项古代盛会就渐渐式微,但如果不是狄奥多西一世将它当作异教活动并在公元394年下令予以取缔的话,古奥运史至少还会比293届、1169年更长一些。
不过,我们也得说,希腊人的自豪只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与他们在欧盟垫底的经济实力关系不大——如果说古罗马人的征服并没有真正割断后来的希腊人与雅典、斯巴达们之间的的联系,那么从东方来的奥斯曼帝国漫长的将近4个世纪的统治在1821年结束时,这个西方文明古国在文化上已经一去不复返地突厥化了,这种情况似乎可以用一样好吃的食物来打个比方——巴黎通街都是的“希腊三明治”,其核心内容却明明是一种叫做“土耳其烤肉”的东西。
悉尼,孤独地感谢西方的赐予
丹麦人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毫无疑问,整个澳洲的人造物里,找不出比它更著名的了,你很难在涉及澳大利亚的任何一段影片里漏掉它那个花岗岩基座上8个大薄壳和2个小薄壳覆盖的形象,当然,在悉尼奥运会自主经营的奖牌背面上,我们同样不会找不着它。
悉尼歌剧院和美国人格里芬规划的首都堪培拉几乎是澳大利亚在建筑和城市形象上的所有象征——这同意大利人皮亚诺和英国人罗杰斯设计的蓬皮杜中心被法国人当作骄傲从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国人几乎是以一种“天朝大国”的心态来面对所有外来文化,而悉尼歌剧院和堪培拉城则可以被视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西方世界送给自己,这个在大洋中享受孤独的堡垒的两件礼物,需要感谢。
因为,和希腊人大相径庭的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很难在文化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尽管这个G8一员远比希腊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像它的移民兄弟美国一样在西方文明中充当主力军——当一个国家足够富裕时,人口就不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了,1940万和102年短短的建国史这样的数字决定了很多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移民国家通常是封闭和开放这对矛盾的综合体,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表现在他们身上就是对邻近亚洲国家的排斥和对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其余国家的认同感上。作为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脱离母体,被强制移植到南半球大洋洲的欧洲文明的孩子,处于黄种人的亚洲和土著的太平洋岛国包围中,澳大利亚人心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孤立感是相当自然的事儿,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不过是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外化。然而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日耳曼世界)时,这样的敌意就荡然无存了,人们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自卑的影子,因此在接受悉尼歌剧院的时候是那么必恭必敬,又不遗余力地把它放在任何一个世界看的见的地方。
巴塞罗那,触手可得的海水和火焰
作为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西班牙人文精神的中心,巴塞罗那是兰色、黄色和红色的。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了1992年那届奥运会上,奖牌背面那个由一个圆点和两条横线组成的具有巴塞罗纳达利艺术风格的跨栏造型的抽象小人,跳跃在会标上就有了颜色,好象海水,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和西班牙富于热情和活力的生活。
西班牙是一个热爱海洋的民族,在他们眼里,海洋是神圣、伟大的,是人类最好的伙伴,而航海则更是一件伟大而高尚的运动,是真正的勇者和绅士的运动。所以,当西班牙人一边追忆着由他们资助,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哥伦布和麦哲伦航海的骄傲时,他们一边把海水的颜色放在了小人图案最显著的头部。他们坚信,精神的发散来自于此。
说到阳光,那是一份至爱,把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引导着整个欧洲的时尚,而西班牙的热情则更是世界闻名了,弗拉明戈舞娘的一袭红衣和斗牛士手中的红色披风决定了红色是诠释这样生活的最佳色彩。当夜幕降临巴塞罗那,霓虹闪亮,它的精彩生活才刚刚开始,喝酒和跳舞可以在整个星期中延续。 因此,小人的身体一半蔚蓝一般艳红。这时,暂时忘记了一栋栋经典建筑以及上面铭刻的伟大名字的西班牙和巴塞罗那显得如此实在。
就像,每天早晨的第一道阳光照在巴塞罗那的标志——位于城市中心,西班牙最伟大建筑设计师高迪设计的圣家族大教堂上;就像,翻开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就像,在博物馆里面参观毕加索的绘画和木刻……想要的文明和历史触手可得。
慕尼黑,小心翼翼地召唤每一份认同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人迫切想给世界一个经济奇迹外的惊喜,于是他们选择了慕尼黑,那个自古以来以桀敖不训的性格和强大的经济后盾雄踞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首府。
要知道,战后德国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国际大家庭认同感,他们尤其需要借这次机会传达自己的意图,为此颇费心思。当德国著名雕刻家、版画家,德国现代主义建筑派别“Bauhaus”的代表人物格哈德·马尔克斯设计了那对双胞胎后,他们的成功了,他们让奥林匹克超越于运动竞技的人文内涵得到了充分体现。
相传宙斯曾化作天鹅,与斯巴达美丽的皇后丽妲幽会,后者生下了双胞胎兄弟卡斯特(Castor)和波乐克斯(Pollux)。卡斯特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之子,难逃死亡命运;波乐克斯是宙斯之子,因而长生不死。两兄弟感情非常好,且各有所长:卡斯特擅于骑术和驯马,而波乐克斯则擅长拳击。当哥哥卡斯特在一次战役中死去后,伤心的波乐克斯向宙斯请求用自己的命换回哥哥。宙斯怜悯他们兄弟手足情深,决定让他们永远在天上长相左右,于是就有了12星座中的双子座……这是一个悠久感人的传说,德国人看中了这一点,他们需要双子座的象征意义——竞技与友谊,用以作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载体,更重要的是,这个形象完全传递了第20届奥运会的主旋律,正如慕尼黑奥运会筹委会主席道默所期待的,让曾有过不光彩历史的国土变得“欢快、充满人情味”,让世界各国青年在这里体验无拘无束的潇洒和饱含情感的真诚。
当然,除此之外,没有人会忽略这样一个意义,这是当时的联邦德国对单独组队在“本土”参赛的民主德国发出的友好与亲情的信号。
转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