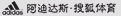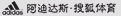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
奥拉克是个猎手,12岁时就徒手杀死了一只北极熊,当那只熊扑向他时,他将渔叉插进了熊的腹部。同年他又捉住了一条鲸鱼。艾皮里是奥拉克的继父,他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是个老猎手,他杀死第一只熊的时间是在九岁,他有着一张笑脸。当他捉住第一只海豹时他还抬不动它呢。西蒙即是艺术家也是猎手,是三个男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又是奥拉克妻子玛莎的侄子。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三个猎手与他们的家庭生活在北极湾的一个小社区里。但是到了六月,他们会在格拉威尔海滨扎营,那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它从北巴芬岛的北岸,深入北极圈五百英里远。 转自搜狐 在打猎季节,我们黎明前从渥太华出发,开始向北的旅途,九个小时后,到达了奥拉克季节冰上的营地。 转自搜狐 我们站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共来了19个游客。我是一个人类学家,我要取得第一手有关生态旅游的资料。这次探险旅游的头是米克,是他第一个鼓励奥拉克家庭成为导游。在1989年9月一个温暖的日子,米克第一次探险了元帅湾,在那个海湾里有上百头独角鲸被喂养着。在岸上是一个因纽特人营地,独角鲸被拉到海滨上。奥拉克的弟弟莫斯刚刚杀死了一只带胡子的海豹,那血污引来了无数的鲨鱼。米克从没有看到自然原始到这样程度。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因纽特人在一起,他开始理解身在雪地里不是死亡的象征,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他想其他人应该有这种经历。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地方的自然景象有着如此惊人的美丽与天然。就是这吸引了奥拉克与他的家庭在克劳福特角扎下了他们六月的营地。在北极的每一个冬天,在加拿大北极圈里岛屿的海都结冰,最后覆盖了六百万平方英里的冰面,是美国面积的两倍。随着温度降到了华氏零下70度,海洋动物中只有海豹还留在这里。北极熊就靠猎食这些海豹而度过那长长的北极寒夜。其他的海洋动物,如白鲸,大头鲸,海象与独角鲸,都穿过了兰卡斯特海湾到巴芬湾与黛卫丝海峡的宽阔海面去了,那是在加拿大与格陵兰之间。春天动物都回来了,一拨又一拨。冬天里只存的10万只哺乳动物在夏季变成了170万只。在这片水域里,它们等着机会去穿过北极。在午夜里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上,褐色海藻在冰下漂荡,数十亿只虾与浮游生物,还有数百万计的北极鳕鱼吃着浮游生物。25万只海豹吃着鱼,还有上千只白鲸与独角鲸。三分之一的北美白鲸都聚集在这里,而世界上的独角鲸每4个就有3个生活在这里。到了6月,兰卡斯特海湾的水域再也没有了冰。但是在元帅湾,那是30英里宽的海口,还保持着封冻。从克劳福特角的营里,用雪车可以沿着浮冰边缘旅行,在冰上观海,听着鲸鱼在风中惊叫。营地里帐篷象军队一样排在高高的岸上。在末尾是厨房帐篷,而另一边是导游住处。冰上有三支狗队。它们欢跳着吠叫着,空气里飘浮着淡淡的海豹肉香味。一个年轻的因纽特人,他是奥拉克的儿子埃里克,在夸着他的雪车,“它们跑得飞快,它们不吃肉,它们也不发臭。 转自搜狐 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帐篷,米克发了绝缘靴子与浅桔色的救生衣。在厨房里,我们与因纽特人认识了,奥拉克,艾皮里,西蒙,奥拉克的姐夫阿布拉哈姆,还有玛莎与她的姐姐库努,她们在厨房里干活。两个都是漂亮的女人,尤其是玛莎,她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有人问奥拉克他们有多少孩子。他开始数他的指头。“十个。”他最后说。玛莎用胳膊肘捅他一下,说了一句。奥拉克的脸红了,“十一个。”他又说。这里没有夜也没有早上,天上是一个不落的太阳。当我们睡着时,要用遮眼罩与耳塞。当我们醒来后,便乘着五个雪橇出发了,向南走去,到元帅海湾去看看那水域,再回到北方去到那浮冰的边缘上。雪车带着我们,三、四个人挤在一个雪橇里,当云雾遮住了太阳时,西蒙解释说,因纽特人研究低云层下冰的反射。水域是黑色的,而海冰则是白的,地面上覆盖的雪与苔原比海更暗。 转自搜狐 当我们到达浮冰边缘后,奥拉克从水面看过去,感到那风打在他的脸上。那是从北方来的,是好事。在我们身后的冰可能裂开,如果是南风那就将把我们都吹出海面而我们还不知道。在这里唯一活着的迹象是一群鸥鸟落在一只被猎人打死的独角鲸上。突然,从浮冰边缘上传来叫声。我看到有四个母独角鲸靠近了海滨,又深入到暗暗的海水中。 转自搜狐 在下个晚上我们遇到了一只北极熊,奔跑在冰面上。我们已经找了一小时的野生动物,这一下子可找到。司机热切地靠近那只动物。那熊生气地狂奔起来。当问到是谁第一个看见熊的,阿布拉哈姆说,“西蒙看见的。噢,对了,是奥拉克,而奥拉克没有说话。” 转自搜狐 在营地里有古代的坟墓,石头是几百年前矗立在那的。那骨头都盖着地衣与苔藓。在那些坟墓周围是生命圈——紫色的龙胆草与矮柳树,死人的营养丰富了小植物群。一个世纪里积累了一英寸厚的土壤。在那些坟墓旁,是一千五百英尺悬崖,在那里能看到兰卡斯特海湾的全貌。那种荒凉与奇异让人震撼。 转自搜狐 西北水道,是在兰卡斯特海湾嘴处,总是吸引着寻梦的人们。名誉与财富的诱惑驱动着人们找寻它,很多人却死于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北极长夜里。1631年,马丁,大卫,与弗克斯在北极圈里没有找到去东方的商业水路。到了十九世纪早期,一些旅游者进入了那片神秘的地域。航海家与探险家都迷上了北极海,那片神秘的冰海。 转自搜狐 真正激发探险家寻求那条水道的原因是在拿破仑被打败后,英国将它的海军人数从 14万减到了1万9千人。到了1918年每三个海员中就有一个军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完成一些惊人的探险。这样他们航行到北极。爱德华·帕利与琼斯·罗斯是第一批探险人员,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因纽特人都谈到了那艘船,宛如他们是上帝一样。整个北极探险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最有名的就是弗兰克林与他的同伴征服北极。这些人不理会因纽特人的经验,如果他们能模仿因纽特人的话,他们不仅能避免死亡,也能获得成功。但英国人遇到了最大的失败。他们穿着紧身羊毛衣,它让汗成了冰。而因纽特人穿着驯鹿皮,松散,毛朝向身体,而另一面挡着风。英国人睡在布包里,都冰硬了。因纽特人睡在冰雪做的洞里,相互裸着身体取暖,这样的雪屋能在一小时里搭成。英国人吃盐猪肉,用瓶子盛的柠檬汁,那瓶子一冻就坏了。因纽特人吃独角鲸皮与驯鹿内脏,两者都有惊人高的维C。最糟糕的是,英国人不屑于用狗,宁愿让他们的年轻人去拉雪橇,那是由铁与橡木制成的。一个就重65 0磅。在它的上面是八百磅重的船,上面是银餐具,雪茄烟箱等等。与他们很多的同伴一样,他们死了,作为一个探险家而名留史册,因为他们保持了他们的习惯,他们不愿意听别人的话。 转自搜狐 渐渐地阳光更暖和了,动物开始活动了。午后,坐在雪橇里穿过冰原,午夜的海呈琥珀色,数万只管鼻鹱在做着窝。在午间吃早饭,在早上四点吃晚饭,在此间睡上几小时觉。那不落的太阳永远明亮,还有那迷人的光环,暗色褪下了,每个人都再也分不出时间。到了第三天早上,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日期,时间也估计不出来了。原始的景象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头七天在冰上,我们看到了鸟与海豹,但是只有一只北极熊,四条独角鲸,一个长胡子的海豹,一队海狮和白鲸。在讨论因纽特人的衣服时,玛莎脚穿一双暗色的海豹皮靴,上面还有一只美丽鹰缝在里面。一个特别饶舌的女人考证了针线,问道,“你是如何找到一张有这样图案的皮的”在晚上,那女人谈到了她去过的所有地方,包括了亚马逊河,东太平洋的加拉巴尔群岛,尼泊尔,南极,现在又到了北极。当她提到波诺时,那是我了解的一个地方,我问她在那里做什么。在一阵窘迫后,她说:“我不记得了,但那里真是有趣。” 我想到一些早期的探险者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个人叫库克,一个美国医生与探险家,他要去北极。1908年在荒原中迷了路,他与两个同伴走了五百英里,靠他们狗的肉维持生命。那里离我们的营地只有一百英里远,他的步枪里只有四发子弹了,半个雪橇,一个坏帐篷。五个月的黑暗使他们生活在阴影中。用骨头做工具,他们杀死了能杀死的一切,用鲸油点燃的火炬,烧着了攻击他们的熊的熊爪。在二月里他们看到了第一个白天,他们要逃出来。靠着腐烂的海豹皮换上新的皮毛鞋,他们又走了三百英里远,穿过了巴芬湾,到了格陵兰,终于得救了。在50年代,加拿大政府在北极地区里建军事基地,因纽特人被迫搬到了无人居住的地方。而其他人则为冷战工作。家庭能得到钱,孩子们开始上学了。游牧营地消失了。有了医疗站,学校,教堂与福利院。政府给每一个因纽特人都发了号码,一些因纽特人的狗都借光登记成了加拿大公民。半个世纪过去了,因纽特语言仍然在用着,男人仍然是猎手。他们用陷井捉野兽,做着雪房子,知道草药的力量。他们也有自己的船,雪车,电视机,卫星电话。有些人喝醉了,有些人进了教堂。 转自搜狐 加拿大最后认识到在因纽特人上遇到的挑战。在1999年4月1日,因纽特人的家园将被从加拿大西北省份中划出来。包括巴芬岛在内,一共才有人口两万六千人,而这里的土地大得有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合起来一样。有人现在提议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因纽特政府。有人说这将是最没有经验的人来治理的政府。 转自搜狐 一天天过去,冰融化了,海湾里满是碎冰。在我们要离开的一天前,独角鲸与白鲸终于来了。奥拉克先看到了他们,整个营地都喊叫起来。奥拉克向前走着,试着路上的苔藓。时间是精密的,此时冰成了因纽特人猎取独角鲸时最危险的东西了。在我们小心地往前走时,那明亮的午间太阳还挂在天上,冰随着我们的体重在变形,有人问西蒙当营地漂浮在海上流动时,他是否到外边去。”他回答说,“你在早上醒来时,就得跑起来象个兔子。” 我们听到了白鲸的第一个信号。这里有上百种生物,白色的如同珍珠,漂浮在洋流上。独角鲸在它们中游着,把鳕鱼赶到水面上来,那些鱼都失去了知觉,浮在水面上。飞翔的海鸥在冲入到水面下猎取着食物。在我们脚下一只独角鲸打破了水面的平静,奥拉克脸上露出了笑意。在中世纪独角鲸的角价格就是黄金的20倍。在全欧洲,只有50个完全的鲸角。 转自搜狐 奥拉克只知道独角鲸春天来,从这里我们知道了猎人所具有的耐心。耐心也许是因纽特人最经久的财富。有一个故事说,格陵兰的一伙因纽特人徒步走了老远的距离,来到一个绿荫的谷地收集野草。当他们到达时草才刚刚出芽,因此他们就在那里看着,等着草长大。我从奥拉克的脸上看到了耐心,当时他在看着第一拨移居的动物到达。我问他是否明天会去打猎,那时我们走了。他的眼睛放着光,“噢,是的,”他说,“我们会的。” 张若愚 转自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