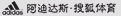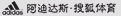大路和远游客--我真的出发了(作者:中途岛)
四辆车,19个人,老巴拉上了他的两个挑担三哥和尕旦,专业司机。老巴夫人带了她的两个姐妹--四姐是穿警服的,精通维语;丽丽是医生;嫂子是电视台的(这回我的摄象机可找着专业人士了),拍《望长城》的那个焦建成是她表兄;锡伯族。车里还塞进了老巴的儿子小巴(今天老巴三次点名都忘了算他),队伍一下壮大了。
刚出市区就整出了第一个花絮。当时是技术顾问风沙星空作头车,队长老巴压后,我作老巴的副驾。迎头看见一个路牌,距库尔勒180公里。我抓起研读了不知多少遍的计划,不对吧,按这里程和速度足可以在库尔勒吃午饭了,向往了多日的翻越冰达坂居然这么简单?
我看老巴,他也茫然。跟着前车左转,又是一个路牌,距库尔勒360公里。这下老巴不干了,抢过对讲机就质询风沙,为什么越走越远,转了没200米一下多出一倍路程。风沙不紧不慢地答复,第二个路牌是对的,其他问题你去找乌鲁木齐交通部门反映吧。
在“黄金走廊”停车。这名字是我编的,因为两旁钻天杨的叶子都是金灿灿的,树冠在头顶相汇成穹顶。照相枪响成一片,连风沙指着对面的山势说这是新疆特有的马蹄形褶皱地貌都少有人听。山脚那条小溪唤作乌鲁木齐河,天山的融雪。
我没拍,只带了四卷,才刚开始呢。
进天山了,感觉不是我们在向上升,而是乌鲁木齐河在向下切,切出一道深谷。平均不到10秒钟就有人赞叹真美。老巴说在内蒙看云都低得很,天山的云永远都是那么高高的。
转弯很多很急,我只顾看路没留神河谷从左手换到了右手。头车不断报着海拔和路况。2000米。3000米。没觉什么不适,也许全被新奇和兴奋所压倒。
大概在3400米处3号车趴了窝。发动机的高山反应。刚出发没三个小时就出状况,老巴急得甚至想用三辆车一齐使劲把它拖过山口。最终决定它单车原路顺坡蹭回去换一辆走干沟赶到库尔勒会合。两个挑担儿和三姐妹暂时向大伙挥手告别了。剩了三辆车,有点孤独感。
冰达坂的老虎嘴,车载高度计显示海拔4018米。我从一号冰川的标志牌前就开着摄象机对着那片洁白不舍得停(嫂子走前紧急培训了一下),想煽情却只剩了一句话,我决定做这趟旅行实在太英明了。后座的影子一声不吭地记在本上。
正对冰峰停下来。丁澜大叫可不可以在上面写字,可不可以去拿一块。我说不出话,那种占据了整个视野的纯真让我无言。
如果真的可以拿一块,如果真的可以在上面写字,我会采一小片晶莹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角,面对着物欲横流朱门酒肉声色犬马烟花巷陌等等新潮时尚轻轻深深地刻上:
让我高筑家园。
这是我大学时的文友(因为我们除了文字就再没其他话题)冷文生的前女友后来的夫人苏纾在毕业之前写的一首诗。我多年前最后一次见他们两口子是在我的母校人大附中用澡堂改装的宿舍里,二人认真教书之余也饶有兴致地弄些儿童文学。不知他们在现今的世道里有什么改变。我这些年每次出门面对陌生的风景,总会不由自主念出这诗中的一句:
让星河在远天游荡吧/山脉/在平畴外延长
向下盘旋了。风沙说这是天山南麓的牧场,巴音布鲁克的边缘。景色自有一番不同。浮土很多,尾车常常被迫减速否则就要吃灰。我把摄象机伸出窗外拍前面扬起的尘头,以及其中模糊的暗影,想象自己是非洲军团的坦克手。
接着就遇上了很经典的“树”的故事。做尾车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老巴也是个酷爱摄影的家伙。这一路我们已经多次私停拍照,给头车的理由便是躲开灰尘。最后一次重新上路没三分钟左侧乌拉斯台河谷中一棵孤独的树突然冲进视线,上半截已经枯死,下半截却还披着灿烂的金黄。全体一致向老巴要求再次停车。
老巴盯着树,把车速放缓,两秒之后一踩油门。算了去追队伍吧前面还会有更好的。没过两分钟我们就与前车鼓角相闻了。老巴这时嘴里一边念叨着怎么那么快要不咱们回去,一边松开油门准备刹车,仅仅一秒后他的脚依然又踏在了原处。
我们后来直到晚上宿营再没遇到过一株可以那么让人回味的树。
我懒得重复由此产生的很程式化的感慨,我只是感受到了一点成熟男人的内心边缘。
走在路上,他或许会被路边的美好吸引,会慢行,甚至有时还会驻足欣赏。但他从来不会忘掉要走的路,不会忘掉真正属于自己的还是在路上。
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冲进巴仑台镇。老巴急于追赶队伍穿镇而过,冲过300米后幸被追回。但就多了这300米让我发现了邮局。连忙趁小店的拌面还没端上来请了假去发明信片,影子陪同前往。归途中迎头撞上Meiemi 也要去,就开玩笑说你咋也有这毛病,早说我就给你代了,她白我一眼,用广东普通话唧唧喳喳:我怎么知道你也有这毛病。
吃罢很实在的拌面,又吃随车带来的西瓜和葡萄。好象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获得了一个新称号“装备”,我在第一时间向他们提供了切瓜的英吉沙和修车的瑞士刀,然后还拿出一排牙签来问美眉们是否需要。大家都倒。这些还都是我从腰间以及斜挎在胸前的小包里取出来的。有人就开始惦记起我那撂在车上的100升大包了。
再说下面一个经典。“超车”。本来行车序列很严格,不准飚车超车。出得巴仑台没一会儿,老巴就说不对了,2号车一直跟的是辆和头车长得一样的三菱,头车早没影了。可2号车又没有对讲设备(一对大个的出发没半小时就歇了,班干部支援我的那对6200到现在也没调出来,只有无去来处的一对4500配备了首尾两车)。老巴冲到平行位置,我照博奕打了个特种兵的手语,他心领神会一加油就过去了。
可就在这一瞬间老巴发现被超的三菱后窗赫然贴着他亲自主持设计的“古道穿越”的车标。这不就是头车嘛。
距离一下拉开了,开始狂追。我分析博奕和副驾佐罗恐怕正偷着乐呢,跟中间夹了一整天实在是憋坏了,当然愿意奉命将错就错。
追车的过程中遇上了两群过路的羊,从车窗中伸出手去可以摸到羊毛和羊角。我朝骑在马上的哈萨克牧民甩了个巴顿式的敬礼,他朝我笑。
亏得有条岔路他们拿不准只好停下来,否则我们今天怕是得到了库尔勒才能撵上。从车上下来我看着风沙哭笑不得,老巴一劲儿解释道歉,博奕、佐罗一脸无辜,几乎乐岔了气。
黄昏时冲进一片大戈壁。心胸随着视野一起开阔。真是觉得新疆这地方无论什么时间什么所在,一抬眼都是风景。
开都河,就是《西游记》里的流沙河,一条河沟嘛。我背着你也能趟过去。
然后又上了一条摇来晃去的波浪路,后座阵阵稀里哗啦,然后就听见了小巴语录:“天上不掉馅饼,掉狼(馕)”。
等到停车分左右唱歌的时候三辆车交流了一下,又多出了掉睡袋防潮垫哈密瓜等版本,取材于各车后部物资不同的摆放方式。
转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