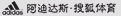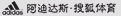梅特·狄金森,英国极限影片制片人,1984年进入BBC受训并作节目经理,1988年离开成为自由导演。1996年5月10日开始,珠峰一带因暴风雪,8位登山者遇难,随后又有3人遇难(此事件记载于《进入稀薄空气地带》)。走运的英国登山队中,梅特·狄金森和专业登山家阿兰·金克斯艰苦卓绝地登上顶峰,并拍下他们渴求已久的记录片。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灾难,痴迷、极限和凯旋的故事。这里节选的是登顶部分。
转自搜狐
□步步惊心过冰脊
转自搜狐
风大起来了,我们才走了一半,只有更努力地推进。一有机会停下来喘口气,我就向北方张望,那是暴风雪来的方向。大朵的云块快速聚集,但是威胁还远没到达这里。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珠穆朗玛峰
转自搜狐
由于如此沉醉于登山,我忽略了我的相机,我那小巧的奥林巴斯装着新电池和一整卷胶卷,会有什么问题呢?
转自搜狐
这条路把我们径直带上了那刀峰般的脊冠,我们抓紧时机沿冰脊快速走过以逃离狂风。我以前总也想不出登山者怎么会从山上被吹落,现在终于领悟了。曾有两名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在这里遇难,他们的身体或魂魄也许就在附近。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这是令人毛发倒竖的一段路。有几米,还要经过一个冰裂缝。两个夏尔巴人远比我们敏捷,轻松地过去了。我每一步都把心提到嗓子眼里,巴望能有处落脚,让我凑和着能挂在这山脊之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8:30,我们到达了第二台阶。这又是一个峭壁,更陡,更长,而且周围没有别的路。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翻越第二台阶
转自搜狐
远在70年代,一支中国登山队曾在这个峭壁最险峻处修了一个简易梯子,却被不久前的暴风雪摧毁了。印度登山者和夏尔巴助手在原来的地方又修了一个梯子。于是“梯子”这个词一直宽慰着我;谁不会爬一个梯子?在我的大脑里,那架梯子简直抵消了整个第二台阶的艰巨。然而,那个我一直坚信不移的梯子,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麻烦。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在第二台阶的脚下,两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发生了。第一是我在头一天晚上用雪熬好的两瓶果汁,虽然紧贴皮肤放在羽绒服里,却全冻成了冰坨,当时我感觉到了不好,但随后的一整天,我才充分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另一件难料的事是,阿兰竟侧身对我说:“打开我的包,把氧气开到每分钟4升。”现在阿兰的身体已被灌进双倍于我的氧气了,我理解他渴望更多氧气来对付这第二台阶,可他的要求还是让我暗自吃惊。我们都十分清楚用氧过高的冒险性,你的身体在双倍的快速供给下处于高水平运转,一旦氧气停顿,等待他的将是急剧的崩溃。我心中划过一闪念,他不只是一般的疲惫,难道他真实的情况比我能感觉到的要艰难许多吗?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开始的几米还可以,不知是谁在这装了根绳子,我尽力伸长胳膊,奋力抓住绳子向上攀,心里充满感激。冰爪像上树的猫爪一样插入石中,我踩在右边一块突出的石头全力接近那梯子,一边咒骂着不济事的冰爪。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停下来好一会儿以便喘上一口气,急剧的心跳带动血液冲撞我的脑子,我感到脉搏比以前任何时候跳得都快,呼吸狂野得失去了控制。有一个惊慌的刹那,我甚至认为氧气中断了,但接着听到那令人鼓舞的嘶嘶声,便告诉自己冷静下来。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正站在马拉里和欧文生前被北COL营地的望远镜最后捕捉到的地点,他们1942年的攀登可能是战前最伟大最艰难的努力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那时候这里没有梯子,前行时只要其中一个滑倒,必定也把另一位同伴带向死亡。我一直逃避对那恐怖的最后的时刻的想象。现在站在这儿,可以毫不困难地感觉到那致命的一跤,那攀登中最无助的一刻。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足可致命的梯子
转自搜狐
我幻想的梯子是下一个障碍。把手放在上面能感到它在左右晃动和前后地拍打岩壁,我怎能奢望它是固定的物体呢!而我冰爪上面的金属钉意外地拒斥梯凳,不但不让我落脚,还无法下视,只能对着脸前的东西眨眼,我不得不凭感觉尽量让我的脚能落到实处。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呼吸又加快了……大量的水汽凝结在我的面罩上。爬到梯子一半的时候,我几乎看不见了,不得不把风镜推到头上。我们都清楚雪盲的危险,可是这种要命的关头,我没法不冒点险。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那梯子先天性地向左歪,并在固定它的背包带和钉子中令人心惊地摇摆,要想抱住它可真得豁出极限的体力。我几乎不能握住梯凳。你用什么描述这梯子都行,就是别用“友善”。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终于到达梯子顶了,下一步也好不到哪去:一个只能靠臂力越过的地方,这个需要人飞荡在上面的突起标志着第二台阶的尽头。要想解决它,只能拉住绑在一个让人半信半疑的铁锁上的一根正在朽坏的绳子,象黑猩猩一样把自己荡到合适的地方。当身体没有物体支持的一刻,我才意识到最悬的时刻就是只靠臂力在北坡上“飞越”。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胳膊的肌肉组织在迅速衰竭。我知道在我衰竭到必须后撤之前还能再试一次,也许两次。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成功了。上去之后,两臂迅速无力。我跌跌绊绊地过了余下的几米。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向冰点屈服的相机
转自搜狐
在这里珠峰第一次露出全景。拍第七张时,奥林巴斯相机彻底罢工。就像我那个在4号营地已向冰点屈服的尼康F3一样。最后我拿出在加德满都花8美元买的玩具相机,这是我唯一的摄影设备了。商标上是一个晒成古铜色穿着比基尼打沙滩排球的女人。我开始透过一个塑料洞取景拍照时,觉得滑稽极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有一两次,我俯瞰我们上来的路,看见阿兰那大红色防风服的身影,远远地落在后头。他还是一分钟4升……而且越来越落后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冲击第三台阶,那是攀天的路
转自搜狐
第三台阶不像前两个那么困难,但海拔更高了。在它上面是珠峰最后一段陡峭的冰雪之域。我卸下背包坐下来,脚跟踏进冰里防止滑倒。我从羽绒服里掏出水瓶,指望它已奇迹般地化了,但这样的温度,你能指望什么呢?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愚蠢,把那两瓶冰扔到废弃的氧气瓶旁,解脱了两公斤。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阿兰在下面远处一个空地上休息,我拿出相机拍下他仰天躺着的镜头。在不远处是一个印度队员的尸体。等阿兰上来,我们就要冲顶了,拉帕越来越担心天气,风更猛了,从顶吹下的雪流割绝了我们向南的视线。空气中充斥着羽状的飞雪和只有高海拔强风才能发出的不祥的嚎叫。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在冰上走了一段,拉帕猛然拉住我的胳膊在风中喊道“阿兰呢?阿兰没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现在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把登顶推向飘渺。天气的威胁在增大,大家都看着我做抉择。我们能不管阿兰吗?那一刻,所有的场景在我脑中快放,我就是不能接受阿兰出问题的可能,我又迷惑又吃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感觉像一个世纪,但可能只是三四分钟。我的大脑在斗争,幸运的是,神经还在保持运转。我闪过种种可能,觉得他不会滑坠,他在这方面的技术太好了,而且他氧气充足,不可能耗尽。也许,正在休息或整理他的装备。 这是一个逻辑性的答复。停顿使我的身体麻木僵硬了,我做出了决定:我们要继续登顶!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一个内在的声音甩给我不舒服的几个问题:难道你不该回去看看吗?难道你不考虑在这儿一切都不能确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吗?我让自己回到镇定的逻辑状态,扑灭那些怀疑的灰烬,我应该相信他一向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也能独自到达顶峰!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那最后的一小时,我的全部身心只有一个信念:到达世界之巅的热望。狂热充满了我的身体和灵魂,让我觉得机械的攀爬不怎么费力,但我知道我的体力快到衰竭的极限了。此时,夏尔巴人已经累了,拉帕惨白的脸活像一节快耗尽的电池。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8750米,只有100米了,垂直的100米。峰顶太倾斜了,新近的雪崩碎片,像汽车一样大,就散布在附近。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抓紧一条看起来在那已有十多年的绳子,我小心地前移,踏掉的东西纷纷垂直地向下滚落,它们逃出我们的视线径直跳下深渊。我的脸贴着石壁,尽量把体重下压以防跌落。猛烈地吸氧让眼前发黑,几乎昏倒。一等到重获镇定,我又沿着这朽木般的山脊上行进。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大约20分钟后,我们出现在顶峰的最后一个坡上,已经绕过了积雪带,又升高了50米。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与最高峰一步之遥
转自搜狐
迂回中,风又大了,那峰顶衬着纠集的云朵,就在我们上面。无常的风发出呼啸的声音。20米之后的冰坡,是那最后的冰顶。没理性的冲动攫住了我:就几分钟的路了……
转自搜狐
这是暗藏的高山病快发作的前兆,荒唐的念头往往是第一步。从帐篷出发8个小时了,我没喝过一滴水,我的身体正在脱水。可我无可顾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到达了脊冠,我很吃惊这不是我想象的最后几步,而是最后一个坡的开始,真正的顶峰还在远处的尽头。这是个诡计。风始终如一,却更猛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顶峰就在几百米远处。我跟进到拉帕后面的位置,开始穿越坚冰。这正是我希望的戏剧式的渐进:右边,山壁垂直向下10000英尺,PUMORI7165米的仙女峰和其它喜玛拉雅群山一览无余。再低处是棕色的贫瘠的青藏高原,起伏的大地依稀可辨。左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羽毛飞旋的白云团状,脚印和冰爪痕迹都失去踪影。我们宁愿从右侧上,那儿能辨出岩石,可以避免踏在伸出的冰檐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再次拿出塑料相机,成功的喀嚓声勾起我的另一桩担心的事,到了峰顶,摄像机还能用吗?峰顶的镜头是片子的最终目的。以前我的相机就在关键时刻坏过。我默默许愿,祈求一切顺利。另一个阴影是,没有阿兰,登顶系列片就失去了意义。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蹈上世界峰颠
转自搜狐
奇怪的风,越接近峰顶,风越小。一开始时,我们被逼的不得不顺风倾斜,以免被击倒,可是现在,冲顶的最后几步,风奇迹般的溜走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终于把手放在主峰的标志竿上,把自己拉上了世界之巅。惊奇地,我发现自己哭了,这是长大成人后我第一次哭。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回头看去,明玛和加增都上来了,还是不见阿兰。我们四个站在珠峰上,却没有宽余的地方。这儿被西风雕塑着,只有一个台球桌那么大,南北倾斜,向东伸出一个突出的石檐。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拉帕取下外面的手套,欢叫着上下晃我的手,我们依次握手,用衰弱的喊叫庆贺。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被一群8000米以上巨人环绕的珠峰,在我看来仍然是惊人地高,一旦你站到上面,珠峰就再无须和群峰比较,她完全地俯视一切,珠峰用不着挤进喜玛拉雅心脏的地位,只需用与生俱来的高贵统率着小表弟们。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把一条腿放在南坡,一条腿踩在北坡,跨着峰顶的鸡冠,尽力把冰镐插进地球的外壳,从技术上说,我精确地站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线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面前就是合金的珠峰标志竿,上面系着一串彩色的三角旗,紧挨着标志竿是一些奇怪的金属牌,可能是以前的测绘标,还有两个橘红色的空氧气瓶。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联想到我们的氧气时刻在减少,我从明玛手中接过摄像机,屏住院呼吸按下开关,透过邮票大的取景镜向外看去,正是我不顾一切来看的景色。摄像机在完美地工作,伟大的EUREKA!正常运转在世界之巅!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坐着拍摄,拉帕在试图用步话机和大本营联系。我收进镜头关上了摄像机。他刚把话机递给我,就听到加增的惊叫,顺着他伸出的胳膊,我看见阿兰正在向我们走来。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再次拿起摄像机,一切简直太完美了,我能拍下阿兰怎样登上珠峰,然后拍他和大本营通话,下面的肯在拍大本营通话那一头的布莱恩,我们能剪辑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珠峰系列片。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紧紧地握着摄像机,我对准阿兰,拍下他缓慢沉重地向我们走来:每走几步,他就停下喘气。我的心跳加快了,不是因为缺氧,是因为这绝美的时刻,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就坐在这里,珠峰之上,拍摄一位世界上最好的登山家奋力走向神圣之地的最后几步。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没有事先的作戏,没有场景的布置,这正是我们要的珠峰片 我的珠峰片……
转自搜狐
“干得好,阿兰,我们成功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终于,在世界之巅!”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阿兰长喘了一阵,他的双肩陡然落下,看起来筋疲力尽,但说话还算清楚。拉帕把话筒递给了他。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布来恩!听见了吗?我在顶峰上!”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是那个约克郡少年吗?感觉怎么样?”布来恩轰鸣的声音,“我在大本营,你看见我了吗?我在向你挥手!”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阿兰回头向冰川下看,景色太宽广了,我们辨不出哪是寺院,那几个小帐篷应该有16英里远呢!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看不清,但我能想象出来。”“我们为你们骄傲,你们两个大英雄,夏尔巴助手们也是。安全回家别忘了为世界和平许个愿!”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阿兰在拍摄我,我在简短地和布来恩通话感谢他,因为他是整个登山队的动力,还有片子,是他对珠峰的激情把我们所有人带到了这里。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们最好离开这里。”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氧气变弱了,我们比预想的在珠峰上的停留要长,50分钟过去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最后看了一眼尼泊尔,我们踏上了向6号营地的归程。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回归 走出死亡的阴影
转自搜狐
对我来说,下撤是一场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噩梦,过去的50个小时,我只在酷寒中睡着过5个小时(后来的30小时一点儿没睡),我在疲劳中苦苦挣扎。冲顶在体力上的消耗远超过了以前我做过的任何事,冲顶中的14小时没有一滴水,这意味着我和阿兰正徘徊在慢性脱水造成的肺水肿或脑水肿威胁之下,冻伤于我已经不可避免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下来比上去危险。脸看不见身体,因此滑倒的机率比上坡时要大。地狱般的冰爪,咔哒咔哒地落在北坡又松又滑的岩片上,好几次,我都险些跌入10000英尺的悬崖。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山脊看起来永远没有尽头,在一个垂直的地方,我集中精神把8号登山器装进绳子,又扣进我的安全带,然后放弃了平衡。我在空中悬着左右荡,膝盖狠狠地撞在石头上,有几秒钟,我快晕过去了,身心全被召进睡眠的暗处,于是红色的警灯闪烁,我强迫自己站起来继续走。我越来越昏溃,没发现阿兰从我身边经过,走到了前面。阿兰一直或远或近和我在一起,总在一绳的距离等着我。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到6号营地的最后100米竟然花了一小时。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氧气早用完了,我全没注意到。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们刚一到,身体里的警报就全拉响了,我的颅骨突突地乱敲,再不喝点什么,我很快就要失去意识而昏厥。问题出在身体上,意志已无能为力。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西蒙刚从5号营地上来,也没有水。而且看上去累极了,他虚弱地和阿兰握了手,就一屁股坐下去。我问他夏尔巴助手烧没烧茶,可他不知道。阿兰向他们的帐篷喊,但没有回音。我将就着脱下背包,蠕动进那冷冷清清的帐篷。阿兰在后,我只记得我像孩子一样喋喋不休的要水。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救救我,阿兰,我不好,我快不行了。快点上炉子,伙计,我快完了。”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阿兰茫然而缓缓地移动着,开始了那注定永恒的程序,我已经能看到一阵阵黑浪涌上来,
转自搜狐
便竭力压下去以保持清醒。然后听到脚步声,是桑迪普,刚从5号营地上来,像西蒙一样衰弱,有些打晃。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你还有水吗?”我问。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他摘下氧气面罩,说了句什么。我看见他系在腰带上的水壶,就指着它,我的脑子突然来电想说一个长句子。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我要水,桑迪普,我不会全喝光但是得喝一点,不然我就完了。”这是我想说的话,可说出来的却成了一串令人费解的胡言乱语。但桑迪普明白我的意思并把水壶递上来。我喝了三分之一后递给阿兰。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
半个小时后我们喝上了第一杯用雪煮化的温热的水,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相信,我将会继续活下去。
转自搜狐
转自搜狐